
十月获稻
之 秋(市融媒体中心)文/图
秋深了,稻谷就黄了。
一望无际的田野里,稻穗齐刷刷地低下了沉沉的头,叶子却倔强地挺立着,将刀锋一样的尖刺向天空。
父亲蹲在田埂上,伸手从田里抽出一根稻穗,放在掌心掂了掂,随后又捋下几粒谷子送进嘴里细细嚼着。许久,轻声却笃定地说:“可以开镰了。”
在农村,春种和秋收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。记得小时候,每年的这两个时节,学校都要放几天农忙假,让学生回家帮忙。
晨 起
清晨,睡得迷迷糊糊的我听见厨房里有动静,便叫醒了弟弟和妹妹穿衣起床。推开厨房门,只见昏黄的灯光下,父亲坐在灶台前生火,母亲弯腰用一双长筷翻动着油锅里的粑粑。
天色黑沉,草木结霜,寒气直钻鼻腔。屋里却暖融融的,炉火将深秋的寒意全部挡在了门外。我们在方桌上喝着热茶,就着一碟辣椒酱,吃着刚出锅的热腾腾的粑粑。吃饱喝足后,母亲把一些油炸粑粑用纱布包了放进篮子里,再放上几颗黄皮梨。父亲从门后拿出两柄早已磨得锋利的镰刀,带着我们走向村外。
田埂上的露水很重,不一会儿,裤脚便湿漉漉地贴在脚踝上,带着一股浸骨的凉。等我们走到田边,太阳正好从东山顶上探出头,一片金黄的稻田像是从混沌里挣脱了出来,赫然横在我们眼前。那片稻田满是纯净的金黄色,黄得那样纯粹、丰腴,几乎要流淌起来。
父亲让我们姐弟坐在田埂上,等太阳晒得暖和些再下田。他和母亲则默默地脱下鞋子、卷起裤管,两双青筋盘虬的赤脚稳稳地踩进了柔软的泥土里。我知道,这个季节的泥水一定凉意刺骨,他们却连眉头也不皱一下。
父亲弯下腰,脊背拉成满弓状,他的左手将一丛稻谷揽入怀中,像搂住一个不听话的孩子,右手的镰刀在稻谷根部往里一递,再往回一收。“唰”的一声,一丛稻谷温顺地倒在了他的臂弯里。母亲紧跟在父亲身后,麻利地把割倒的稻谷拢起,扎成大小适中的稻捆,再将它们立在田里。
一下又一下,父亲不断重复着这个动作。他的脊背一耸一耸地,像一条随波逐流的鲸。不一会儿,父母的身后便整齐地站了一排“稻草人”。
等身上晒得暖和了,我们赶忙下地,捡拾落在田间的稻穗。“一粒米,千滴汗”,父亲要求我们把每一粒稻谷都捡进口袋,连陷进泥里的稻穗也要小心地扯出来。

九河乡稻田。
日 作
临近正午,四下逐渐热闹起来,一块块各家各户的稻田里,上演着几乎相同的场景:大人一边弯腰忙碌着,一边说着无伤大雅的玩笑。孩子们雀跃着,他们哪里懂得大人的辛苦,假装拾稻穗一会儿就丢下活路,一头钻进稻丛里捉蝈蝈、掏鸟蛋。
汗水从脸颊、脖子和后背上不断冒出。汗滴流进眼睛里,火辣辣地痛。我多么希望父亲能停下来,坐下来喝一口水。但他似乎不知疲倦,依旧按照自己的节奏不紧不慢地收割着稻谷,只是偶尔直起身子,用握镰刀的手臂蹭一下额角的汗。每割完一垄稻谷,他的目光扫过身后那一片片已经倒伏下的、整齐的“稻铺子”,眼神里闪过一丝极淡的、难以捕捉的满足。
“一籽落地,万谷归仓”,对于庄稼人来说,丰收或者歉收,关乎全家的温饱,关乎生活的底气。
慢慢地,父亲的背上洇开一片深色的汗渍,蓝布衫上结出了一圈白花花的盐霜。
“歇了,吃饭吧。”父亲终于停下手上的动作,招呼我们走到小溪边的一株白杨树下。周围割稻的人家也都纷纷停下手中的活,找一处阴凉的地方吃午饭。人们相互“串门”,看一看哪家的水稻颗粒饱满,比一比哪个稻种的产量高。
母亲把蓑衣铺在地上,从竹篮里拿出油炸粑粑和辣椒酱,又累又饿的我们忍不住狼吞虎咽起来。父亲和母亲边吃边盘算着:小河边的田湿,收了稻可以点上蚕豆;西山脚的地干,割完稻谷,翻耕一下,再施上肥就让地养着,来年种水稻才能增收;新米打下来要给在城里工作的舅舅送一些,还要做一些饵块捎给远嫁的姑妈。母亲想了想又说,去年吃剩下的米可以酿一些米酒,隔壁婶子就要生了,早就托了她做米酒。
此时,微风轻拂,送来一丝难得的凉意。我静静地在柔软干枯的草地上摊开四肢,顿时觉得舒服极了。
一只黄雀扑棱着翅膀停在半空中,朝着稻田深处不断地鸣叫,让我怀疑那稻田里是不是藏着它的窝?窝里还卧着几只小黄雀?多么惬意的时刻,耳畔是父母熟悉的絮叨、风吹过白桦树发出的“沙沙”声,还有远处田间若隐若现的说笑声,只觉得眼皮越来越沉重,视线也渐渐模糊。
不知道过了多久,我听见父亲说:“走,下地。割稻要一鼓作气,歇多了,气就漏了。”说着,他“咕咚咕咚”喝下一大口茶水,拿着镰刀径直走向稻田。我坐起身,看着父亲和母亲的身影一步步走向金黄色的稻田深处,一阵阵细微的稻浪从他们的脚边泛起,慢慢向远处翻涌,最后消失在远处的山脚。风儿调皮地掀起父亲的蓝布衫,又拂过母亲柔软的发丝,那画面美得动人心弦。
下午,太阳炙烤着大地,似乎要赶在入冬前再耍一番威风。几朵白云识趣地躲到了山后,连风也漫不经心地歇下了。
父亲割稻的节奏明显没有上午那么快了,但动作中依旧透着一股收放自如的洒脱,仿佛他不是在做一件劳苦的活。
空气中弥漫着稻香和泥土被翻搅开后醇厚的气息,这是一种唯有在秋天、在收获的时刻才能嗅到的、教人心里无比踏实和安稳的芬芳。

九河乡风光。
暮 归
不知过了多久,光线渐渐暗下来。
仿佛是接收到了某种命令,割稻的人们几乎不约而同地直起腰,捶一捶酸痛的背。
田野里再次热闹起来,人们割稻的节奏不由自主地加快起来。早割完的人家也不忙着回去,而是帮周围割得慢的人家搭把手。拉着牛车的人热心地招呼大家把农具放到车上。大人们一边收拾东西,一边呼喊着四处贪玩的孩子。
我看到父亲坐在田埂上久久地望着这片收割后的旷野,他的表情是平静的,几乎看不出喜怒。从我记事起,父亲寡言少语,很少见到他情绪波动,仅有一次见到父亲流泪,那是在送别即将远赴河南读大学的我的时候。
杨绛先生的《我们仨》中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:“老人的眼睛是干枯的,只会在心上流泪。”我想,父亲和很多像他一样为生计奔波的人,是不会轻易流泪的,只有生离和死别才能让他们动容,或许他们的泪早已变成了汗。
当我们把所有的稻谷挪到地头堆起,夕阳正将最后一丝温柔洒向大地。
暮色中,人们从四面八方聚拢过来,说说笑笑地往村庄走去。他们的身后是那片空旷的、歇息下来的田野,它像一个产后的母亲安详而疲惫。晚风里仿佛还回荡着镰刀和稻茎摩擦的“嚓嚓”声,那不是挽歌,而是一首沉静的、关于轮回的无字诗。
每年的秋收,我的父亲、母亲,不,是所有乡亲就是这样起早贪黑,一丛一丛地割、一捆一捆地扎、一趟一趟地背,认真地完成一年之中最后的一场忙碌。等所有稻谷、玉米、黄豆、瓜果、蔬菜都归仓,他们会瘦掉一圈,手上的老茧又会多上几个。但他们的身体里似乎有用之不竭的力量,只要饱饱地吃一顿,安稳地睡一觉,第二天又生龙活虎了。
这些可爱的、平凡的乡亲们呀,他们让我学会了朴实、勤劳、坚韧和善良的立身之本。直到如今,我仍然会被那些劳动群体、劳动场面所感动:风雨里身披蓑衣耕作的人群、山脊上负重前行的背夫;打谷场上飞扬的尘土和谷粒、抬重时震耳欲聋的劳动号子……
这些场面总能毫不费力地让我泪湿眼眶。但我不想歌颂,我想他们不需要歌颂。有时候,置身事外的赞美是无力的,甚至仅仅是矫情。我更愿意站在他们中间,体会他们的酸甜苦乐,和他们一起匍匐于大地,用汗水去浇灌赖以果腹的庄稼。
《诗经》云:“万亿及秭,为酒为醴,烝畀祖妣。以洽百礼,降福孔皆。”古人把五谷作为最珍贵的礼品来祭祀祖先、庆祝丰收。我们的父辈又何尝不是这样?一年一种、一岁一收,他们与土地早已不是简单的耕耘与索取的关系了,他们的生命、血脉、悲喜都已融入这片深厚的红土地,春种、秋收、夏耘、冬藏便是他们全部的人生哲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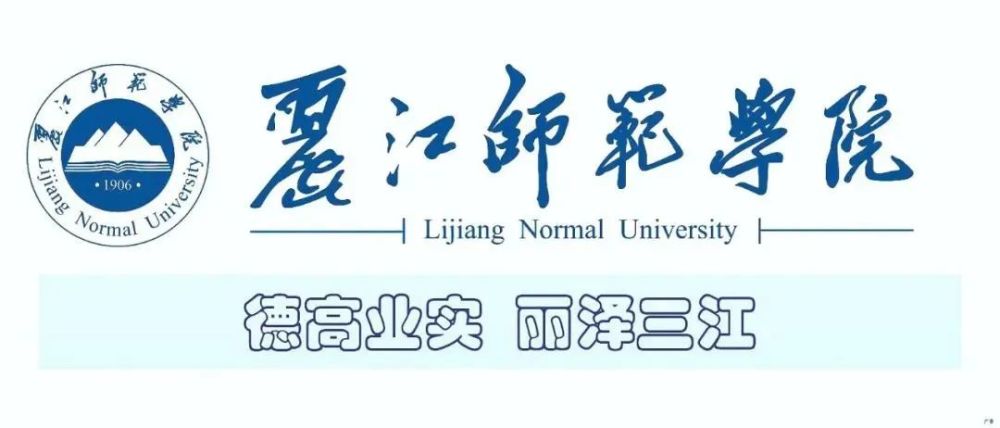

编辑:白 浩
校对:张小秋
二审:和继贤
终审:郭俊燕
丽江市融媒体中心 出品
【声明】如需转载丽江市融媒体中心名下任何平台发布的内容,请 点击这里 与我们建立有效联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