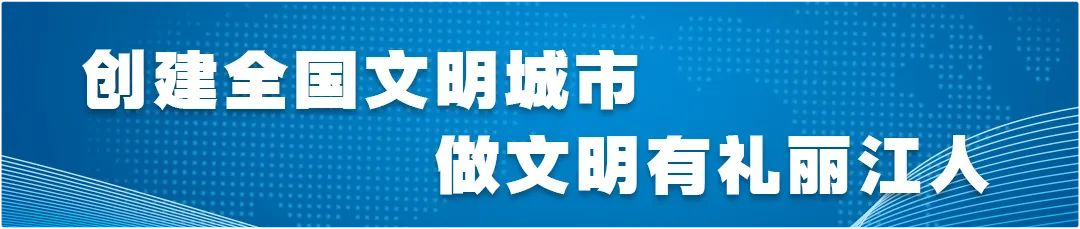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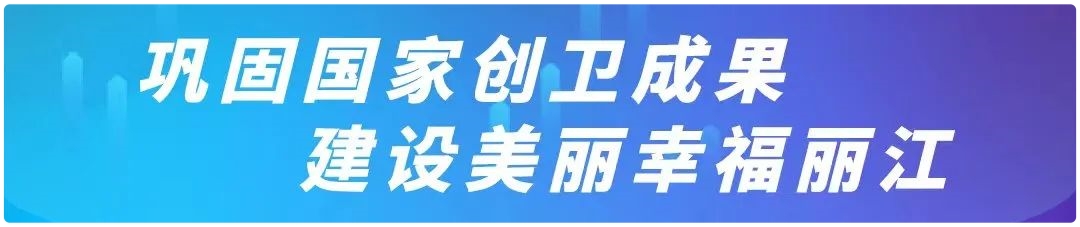
在我10多年记者职业生涯中,采访过许多先进典型人物,刘增元老人是其中很特别的一个。
采访刘增元,突破了我采访生涯中的很多第一次,第一次在采访过程中泪崩失态,第一次为了采访一个人物3次下乡,第一次撰写超过1万字的长篇通讯,第一次忐忑地等待报纸出炉,第一次很想让更多人读到老人的故事……
从在农家小院初次与刘增元老人见面,到《寸草之心报春晖——一个87岁老党员的传奇经历与追求》于3月29日在本报刊发,耗时整整15天。直到现在,那种心里的感动仍久久无法消散,老人瘦弱矮小的身影,他的神色、他说的话,总是不经意间在脑海中萦绕。
因为刘增元老人,章斐这个陌生的小村庄,似乎与我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01
泪崩失态
3月15日,我和同事王鹏第一次驱车前往永胜县三川镇章斐村。
彼时的三川坝绿意盎然,橘黄的沃柑缀满枝头,人们在田野里忙着采摘青蚕豆。
在村里一位老主任的带领下,我们径直找到了刘增元家,没想到却扑了个空,家里只有老人的孙女和1岁多的小曾孙。我们在村子里一边找一边打听,最后,在一块农田里找到了正在摘豆子的刘增元。
在这次采访之前,我已经从其他媒体上零星读过一些关于刘增元的报道,也看过他的照片。
但当老人实实在在地站在我面前时,我还是被深深地震撼了。老人身高仅到我的肩膀,黑褐色的脸颊布满皱纹,一件灰色的长袖T恤扎进军绿色的裤腰里,显得有些宽大,运动鞋里的双脚没穿袜子。
老人不善言辞,但黑瘦的脸上却一直挂着微笑。
没有太多寒暄,回到老人家里,我们找了几个草墩,坐在院子里就开始了采访。

记者在采访刘增元。(杨秀娟 摄)
几年前,老人的听力严重下降,要在他的耳边大声喊,才能勉强听得见。采访的过程非常艰难,全程由同村的长辈在老人耳边大声地喊出问题,再由老人回答。
幸亏老人记性好,表达清晰,采访得以缓慢地进行下去。
在老人断断续续的回忆中,一个个曲折苦痛的故事在我们面前展开。初生被弃、卖骡葬父、雪夜冻昏、两度重伤……老人的叙述波澜不惊,仿佛置身事外地讲述着一个遥远的故事。
听到20多岁的刘增元寄宿在八河村一户村民家阁楼中,因为衣衫单薄差点冻死在雪夜的片段时,我终于忍不住泪流满面。
脑海里浮现出余华的著作《活着》。那一刻,书中主人公福贵的身影竟然和老人合二为一,那种凄惨的境遇和宿命感,如此相像。
3个小时的采访,故事只讲了一半。临近中午,我们邀请老人去吃点便饭,他婉言谢绝了。细问才知道,原来因为早年喉咙受过伤,如今只能吃一点清淡的米粥。
吃了一顿简单的便饭后,接着采访,心情已经平复许多。
临近黄昏,采访告一段落,去看了老人修建的“雷锋桥”。那是一座约4米长、2米宽的便桥,架在章斐村田间的一条小河上。10年前,这座小桥曾为章斐村村民生产生活和孩子求学架起一条通途。如今,章斐村的水泥路已经通到各家各户,这座小桥已经不再是孩子们上学的必经之路,但是很多去田里干活的村民仍然每天都要走。
由于天色已晚,我们没有机会到老人种树的庙箐沟去看看,只能匆匆返回城里。
回来后,我连夜整理、写稿,用了整整3天,架构出稿子的骨架。
那几天,刘增元老人瘦弱、单薄、苍老、腼腆的身影总浮现在我的脑海里,让我时时想:这样一副羸弱的身体究竟是如何承受住了过去的种种磨难?
02
赤脚省钱
3月23日,再次下章斐村补充采访。
这次,孙学敏老师与我们同行。他曾带领《昆明日报》《都市时报》在云南报业领域创下过辉煌业绩,有着独到的采编经验和撰写大稿的过人实力。
这次补充采访,除了核实稿件中尚不确定的事实外,我们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抓细节上。出发之前,孙老师为我们指明了30个需要补充的细节。最终,在实地采访中,我们的收获远远超出了预期。
孙老师让刘增元老人撩起衣服,用手仔细摸他在易门铜矿期间工伤时留下的脊椎骨节错位的地方。找来皮尺为老人量了身高,仅有1.45米。在村里的超市借了体重秤,称出老人的体重是41公斤。这些细节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深入采访的重要性。
在老人家的卧室,我们查看了他的衣柜、鞋子、书柜和日常用品。这些年,因为与儿女饮食习惯不同,老人单独做饭吃,自己有一个简易的小厨房。我们仔细看了他的锅碗瓢盆、橱柜冰箱等,试图用一些生活细节,将最真实的刘增元呈现在读者面前。

87岁老党员刘增元。(王鹏 摄)
整个上午,我们花费了大量时间翻阅老人的笔记,希望找到更多能打动人心的故事。
刘增元老人只有小学文化,他的笔记和他坎坷的经历一样,零零落落,只能半看半猜,在字里行间寻找那些尘封的旧事,每当找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,我们都会激动地交换着看。
老人一直默默地看着我们,话很少,看到我们对这些笔记感兴趣,他又打开一个木箱子上的小锁,拿出另外一摞更加陈旧的笔记本。
中午,章斐村党总支书记胡卫华买了几份盒饭,我们就着老人的小桌子凑合吃了一顿午饭。老人吃得很少,稍微有点油、辣、硬的东西,他都咽不下去,只是简单地吃了一点蔬菜和米饭。
下午,我们决定去老人种了20年树、修了10多座拦沙坝的庙箐沟实地看一看。担心老人体力不支,我们原先不打算劳烦他。但老人执意要带路,出门前,他坐在草墩上脱掉了袜子。
我心中于是了然,明白为什么初次见面时他的脚上并没有穿袜子,原来是害怕干活时磨坏。一个这么节俭的老人,却舍得交万元大额党费,他对党和国家、对人民群众究竟怀着怎样的一份情感啊!
上庙箐沟的路崎岖异常,有些地方其实根本就没有路,年近90的刘增元老人却爬得很轻松,很快将我们落下一大截。
老人边走边指给我们看他修建的拦沙坝,这些没有加钢筋掺水泥的拦沙坝,经过常年雨水的冲刷,已经面目全非,只剩下小部分石墙。
在半山腰,我们看到了老人当年搭建的小窝棚,只有三四平方米见方,棚顶很矮,进出需要弯腰,仅能遮风避雨。
雨季到来前的庙箐沟十分荒凉,黄土在阳光的暴晒下十分刺眼,刘增元老人站在齐腰深的荒草丛中,显得更加矮小羸弱。
在这片荒山沟壑间,老人20年如一日种下数万棵树,只为了不让泥石流冲毁村民的庄稼。
岁月如梭,绿了荒山,白了头发。
在大自然面前,人类是那么渺小,20年劳作只能换取一点点改变。人性又是那么伟大,明明知道前路艰险,却能鼓起勇气出发,一鼓作气坚持,只为了心中信念。
离开章斐村,准备返程时,刘增元老人颤颤巍巍地捧来一箱鸡蛋要送给我们。泪眼恍惚中,我似乎又看到了几年前,那个捧着鸡蛋送给章斐小学的瘦弱老人。
03
三下章斐
采访回来后,在刘增元老人那种“千磨万击还坚劲”精神头的鼓舞下,以往采写深度报道会觉得很辛苦,但是这次却有使不完的劲、道不尽的话,三天写稿到深夜,竟不觉乏累,最终一气呵成。
然后就是不厌其烦地修改,数易其稿,直到过了自己这一关。
3月28日晚,排版、校对、审核、交付印刷,一直熬到半夜12点。躺在床上,心里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,却又忐忑地等待报纸出炉,生怕遗漏什么,或者有什么差池。
3月29日,长篇通讯《寸草之心报春晖——一个87岁老党员的传奇经历与追求》以特稿形式在本报用3个版面作了刊发,全文14000字。据一些老同事回忆,这是本报复刊以来刊登过的最长篇幅的通讯。
拿着新鲜出炉的报纸,第一念头就是想拿给老人看。
正好胡卫华书记组织村里的党员集中学习刘增元老人事迹,于是,我带着30份当天的报纸,第三次驱车前往章斐村。
一个人开车穿越一个又一个隧道,想象着当老人拿到这份报纸,会是怎样的情形,心里暖融融的,似乎连风里都有春天的味道。
上午9点,村委会二楼的会议室里,党员们陆续到达,报纸被一抢而空。
就在活动就要开始时,胡卫华却怎么都联系不上刘增元。
几个年轻的党员分头去找,刘增元的女儿家、集市上、田地里到处找不到。无奈之下,胡卫华只能先组织大家开始学习。同时,派人继续寻找。
在宽敞的会议室里,村里的党员们认认真真地看着有关老人的报道,看到自己熟悉的故事变成了一个个报纸上的文字,所有人脸上都带着一股兴奋与感动。
活动进行到一半时,终于有人在庙箐沟找到了老人,他又上山管理树苗去了。
满身泥土的刘增元一走进会场,众人赶紧将他安排在第一排中间的座位上,一个老党员还贴心地为他戴上了党徽,“众星捧月”的感觉让他一时间竟手足无措。
还是那身宽大的迷彩服,还是那个瘦小的他,当党员代表们一个个发言称赞他时,刘增元老人一直腼腆地微笑着,始终不发一言。
活动结束后,他背上背篓回到自家院子,找了一个草墩坐下,戴上眼镜,细读起报纸来。

87岁老党员刘增元。(王鹏 摄)
“谁言寸草心,报得三春晖。”小草那么平凡,却努力地向阳而生。刘增元老人的一生,就像那棵小草,在夹缝中努力生长,拼尽全力迸发绿意,装点着生养它的大地母亲。当他87岁高龄时,终于被看见被铭记,我想他应该会觉得很幸福,而这一刻,幸福的人又何止他一个呢?
趁着老人读报的工夫,我走进刘增元老人简陋的小厨房,只见电磁炉上的锅里还有半个红薯,应该是早上吃剩下的。电冰箱的保鲜格里有一搪瓷缸米粥和半碗水煮青菜,这应该就是老人一天的饮食。
不一会儿,老人的儿子刘忠华干完活回到了家中,看见父亲正在认真读着报纸,他也找来一个草墩坐在父亲身边,凑近了看。
父子俩默默地读着报纸,阳光洒在院子里,很静、很暖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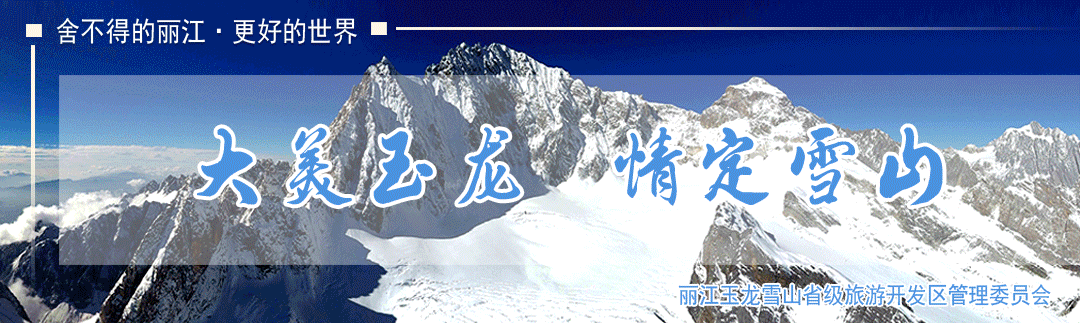
记者/张小秋
编辑/林 彤
校对/李映芳
责编/和众学
终审/和丽星
丽江市融媒体中心 出品
(发稿编辑:林彤)
【法律声明】除非本单位(丽江市融媒体中心)主动推送或发表至第三方网站或平台,任何第三方网站或平台不得转载丽江融媒App及LIJIANG.CN和LIJIANGTV.COM主域名及子域名下之任何内容,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