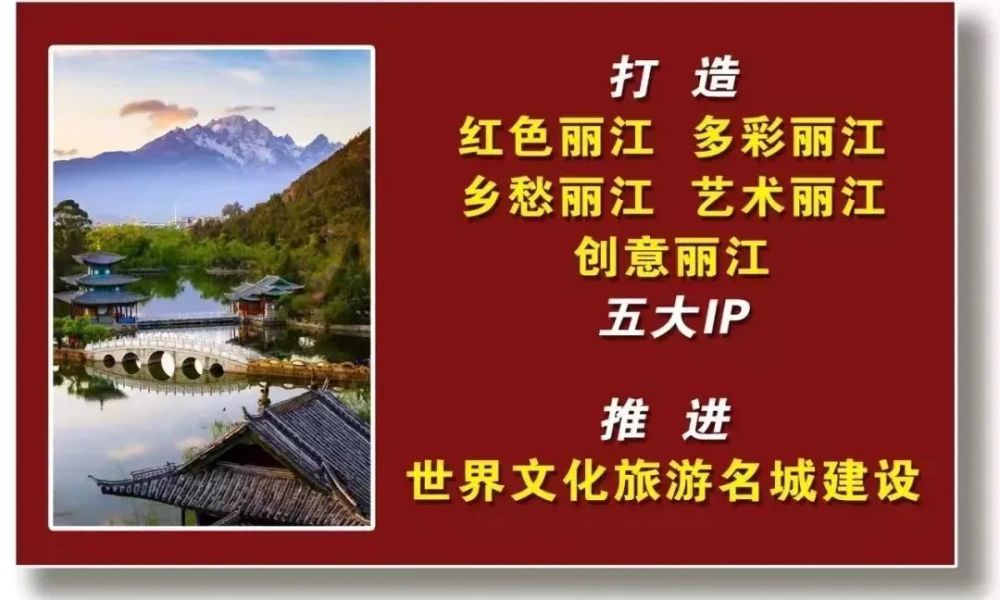
我的祖父和积贤
和钟华(昆明市) 文/图
母校丽江市一中即将迎来120岁生日之际,我的感激、怀念、自豪之情油然而生,同时,祖父和积贤的形象又浮现在眼前。
和积贤(1871年—1908年),字殿臣,清末廪生,抗法名将杨玉科的副将,振威将军和富谷之子。他是清末丽江杰出的教育革新家,丽江府中学堂、丽江府初级师范学堂的筹办人、第一任监督(校长),云南省第一张白话报《丽江白话报》的主要创办人、丽江白话报社社长。
祖父自幼聪慧好学,曾立下鸿鹄之志,然而,面对清廷的腐败,他虽在父亲的影响下潜心攻读经世致用之学,却再无意科考。清末,废科举、兴学校的新潮兴起,云南学院责成丽江雪山书院主理丽江办学事宜。当时,丽江官绅多主张“行事持重,徐观其变”,我的祖父却力排众议,积极主张办新学,并出任府劝学员,得到周兰坪、王竹淇、唐杰生、李怀壁、习彦卿、习祚卿、杨宪元等丽江名士的拥护。他首先借府考棚办了一个师训班,为办新学打下基础。时任丽江知府彭继志思想开明,推崇维新,力主办新学,便委任我的祖父筹办丽江府中学堂事宜,并行文至省保举他为学堂监督。
祖父全力以赴,一边建校一边招生,于光绪三十一年(1905年)招收5年制中学、师范各一班。光绪三十三年(1907年)春,新校舍落成,中学堂招生100名。在经费困难的情况下,他撰写了《劝自费入学书》,规劝学生体谅校方的困难,坚持上学。他与其他热心之士共同努力,还先后开办了丽江县立高等小学堂、女子小学堂等。
《中国少数民族大辞典·纳西族卷》对我的祖父作了具体介绍及评价:“清末丽江革新教育时开办新政的急先锋”“为人仗义,教学上精细入微,要求也极其严格,学生除假日外均不得外出。偶尔发现学生中有吸鸦片者,他即刻向学生朗读林则徐的禁烟奏折,并将吸烟者除名”“彭继志考虑到丽郡僻远,‘须唤醒群伦’,拟议创办白话报,并委托其筹办。他竭力而动,建议彭继志请赵式铭当主笔。彭继志即写聘函,派车马迎请。赵式铭抵丽江后,府署成立官报局、排印所。1907年2月,正式开办丽江府白话报社,他任社长,并亲写《丽江白话报》报名。他白天教学,处理学校事务,晚上就在学堂与赵式铭商讨、编撰白话报。1907年3月,《丽江白话报》第一期出版。《丽江白话报》的主旨为:呼吁民众誓死抵御列强入侵;宣传物竞天择、适者生存,国家亦为是;振兴教育,学习科学知识,反对迷信,提高国民素质;振兴工商业及农业,国富民强;发扬尚武精神;提倡白话文,反对八股文;开放女权,振兴女子教育等。因报纸办得有声有色,适应时势,云南巡抚衙门要求每期寄200份给巡抚衙门,分发给云南省各府、州、县,影响至全省。由于他白天教学,晚上撰稿,夜以继日,终积劳成疾,于1908年6月溘然辞世,年仅37岁。《丽江白话报》因此失去支柱,出至第7期停办,第7期实为缅怀社长和积贤之专刊。《新纂云南通志》中列有和积贤传略”。
早在光绪三十二年(1906年),云南省学院就推举祖父赴欧留学,但因他致力于家乡办学事宜,毅然放弃了这一难得的机会。为了维持办报纸的开支,祖父时常变卖家中的首饰,得到知书达理、深明大义的祖母杨氏的全力支持。

和积贤。
祖父担起了办学、办报的重任,“昼则坐镇学堂,夜则谋划报纸出刊事,累月未归家”,终因积劳成疾英年早逝,乡人无不痛惜。在《丽江白话报》第7期,主笔赵式铭以“精愚”之笔名为祖父写了如下悼词。
丽江和积贤君,任侠士也。两年以来,郡伯巴陵彭公创办新政,得君赞助之力为多。去岁被举为师范学堂监督,苦心经营,不避劳怨。一旦溘逝,士林惜之。
彭公挽以联云:
岂彼苍亦忌英才,百废未兴,何遽夺我指臂之如斯速耶?
是此邦有数人物,一朝常往,能无使余唏嘘而不可禁哉!
悲壮淋漓,感喟欲绝,得此挽语,和君其不死矣。
余有诗哭之云:
儿女依依犹弱小,
桑梓事事赖英才。
即论家况难抛手,
复值时艰忍卸肩。
阅世荣枯归短梦,
催人哀乐入中年。
床头谁共深宵舞,
乍听鸡声一惘然。
同志有挽诗者,望寄赐本馆。拟收集成册,付之排印。鄙人此作,特引玉之砖耳。
赵式铭还作了一副挽联:
剧谈、豪饮、狂歌,两不相离复两不相下;
国弱、时艰、民困,君何忍死亦君何忍生。
赵式铭与祖父在共同的事业中结下深厚的友谊,这些挽诗、挽联读来令人肝肠寸断。
在赵式铭之孙赵衍荪抄录其祖父的遗稿《弢父行年六十自述》中,可以窥见我的祖父与赵式铭的交往过程,以及祖父病逝的概况:二十九年癸卯……冬初与鹤裳游丽江,得交和殿臣。和君名积贤,廪生,劲直有气力,与余一见如旧识……三十三年丙午……六月奉府檄赴郡商榷学务。至则郡人和殿臣、王竹淇成章、周兰坪暐诸君,以郡守彭公友兰莅任一年,甚有威惠,近届瓜代,特假檄促君来丽江府五属联名保留,牍君其无辞。余不得已,为削一搞而归,从而得留任。太守知之,以和君为罗,罗致余幕下,乃许诺俟明春赴郡。三十五年戊申……郡中交友以和殿臣尤投分。尝因事至剑川,余觞之天山观。要同赌酒,余曰:“日在郡中与君痛饮,饮必两醉,何苦乃尔。”君不许,两人果大醉。归至家数月后疾作,不能言,但把笔书余名。余疾往视,一见握余手,卒不能吐一辞。余知彭太守畜有龙涎香,可化痰,遣人乞至,一呷而出语,遂如宿欢,不料其以是夜殁也。
对于祖父的病况,我的堂姐夫司马贾记述如下:“1908年6月末,和积贤因偶感风寒,继而发烧,次子举善为学生,在旁边侍候。见父亲病状,欲回家告知母亲。和积贤不许,说一点小病,不要紧的。到次日,口已不能言语,但仍能握笔写了赵世铭的名字。赵世铭赶来探视时,还起来和他握手,而嘴里已吐不出一个字来。夜里,和积贤病情加重,次子举善翻墙回家报告。到家人来时,已在弥留之际。家人立即用舆轿抬回家中。是夜,和公溘然长逝,时年37岁。”20世纪90年代中期,我的堂兄和之翰回丽江省亲,专程到母校参观祖父修建的校舍。从他那里得知,当年我读书、住宿的那一进两院的老房子,皆为祖父受彭继志之托修建。
祖父白天办学、晚上办报,竭尽心力、积劳成疾,青春之年即辞世,却没能留下半张纸、一个字。痛哉,惜哉。
值得欣慰的是,母校作为“滇西北文化的摇篮”,百多年来为国家、地方源源不断地培养、输送了各类人才,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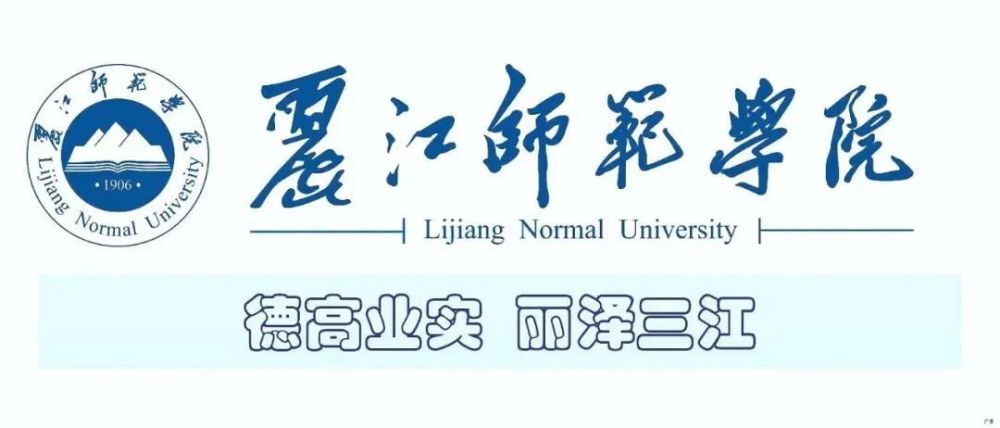

编辑:白 浩
校对:张小秋
二审:和继贤
【声明】如需转载丽江市融媒体中心名下任何平台发布的内容,请 点击这里 与我们建立有效联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