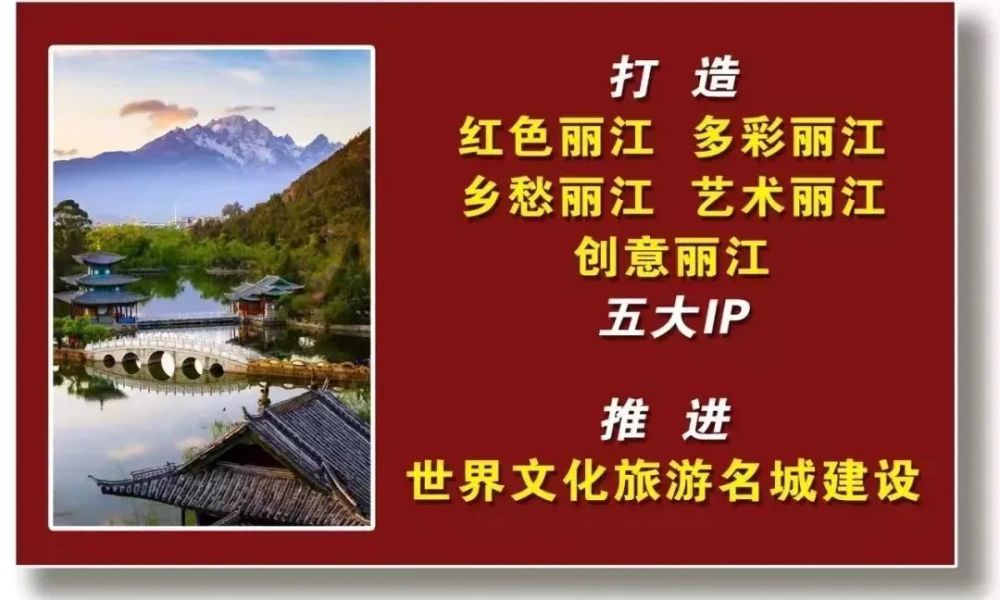
恋山 见山
之 秋(市融媒体中心)
也许是从小在山里长大的缘故,我对大山有一种莫名的亲近,一有空总爱往山里钻。
尤其在心情烦闷、沮丧的时候,喜欢一个人跑到山中,让腿脚带上一些树叶、草屑,让身体饱吸一口山野之气。这时的我顿觉五脏六腑中的浊气消失殆尽。
我家四周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横断山脉,一座连着一座,一片接着一片。祖祖辈辈出生在山里,活着时靠山吃山,死后深眠山中。
我的父亲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农家,因为祖父是一个文弱书生,祖母又体弱多病,一家人经常吃不饱、穿不暖。作为3个弟妹的兄长,父亲早早挑起了养家糊口的担子。17岁起,他就跟着马帮进老君山砍木料,再拉到剑川县城的木材市场去卖,来回走一趟要两三天。
“那时候是真苦、真饿啊。”父亲说:“马帮风里来雨里去,路上就靠几个冷硬的饼子当干粮。有时实在饿急了,大家就剥开松树皮找里面的肉虫吃,或者挖草根、摘野果吃,运气好的时候能打到一两只野兔、山鸡,那可是欢天喜地的大事。”
年少时的父亲瘦高个子、白净脸庞,村里人都说他像书生。他常穿一件缀满补丁的上衣,套一条宽大的棉裤。用绳子扎得紧紧的腰身跟姑娘的一样纤细。跟着马帮跑了没几年,父亲逐渐变成了一个脸膛黑红、手脚粗壮、胡子拉碴的赶马汉子,再无半分书生的模样。
父亲还没有开始体验青春的懵懂青涩和无忧无虑,就已经饱尝生活的苦楚。但父亲身上顶天立地、任劳任怨、踏实可靠的品质,也正是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一点点养成的。
父亲20岁出头时和母亲成婚。新婚没几天,他又匆匆进山伐木料、割板子。母亲则在家中辛苦操持着一家人的生活。父亲经常四五个月回不了一趟家,即便回来也待不了几天。我不止一次听母亲讲我出生时的经历:那是在桃花即将盛开的初春,母亲临盆在即,父亲却杳无音信,大腹便便的她每天都要到村口走一趟,她多么希望丈夫能赶在她生产前回到家。可是,直到她在床边的一件蓑衣上艰难地生下第一个孩子,父亲终究未能赶回。后来,弟弟、妹妹相继出生时,父亲也都没有在场。
母亲对父亲既有怨气又心疼。母亲会在父亲出门时说,是山里的妖精把父亲的魂勾走了;父亲回到家,她又看着那双满是伤疤和老茧的手心疼得眼泪直流。她说:“孩子他爹,不要进山了吧。再去连命都要没了。”父亲听着母亲絮絮叨叨,也只是叹一口气,始终沉默无语。到该进山的时候,父亲依旧雷打不动地动身了,因为家里有七八张嘴靠他吃饭呢。
儿时的我竟然真的相信山里有妖精。那是因为,我的一位堂叔从深山里娶回堂婶时,新娘子俊俏水灵的模样几乎震惊了村里的男女老幼。老人们说,这姑娘算得上十里八村的第一美人。我的这位堂婶身材修长、肤如凝脂,一双乌黑晶亮的眼睛里仿佛盛着亮汪汪的湖水。她说话轻柔、亲切,笑起来脸上就漾起一对酒窝。那时候,我曾傻傻地猜测,书里写的勾魂夺魄的狐狸精大抵就是这样吧。有时我又想,这位温柔的堂婶不可能是狐狸精,而应该是一位饮露食花的仙女。

群山绵延。
年幼时,我总觉得周围的一切都很灰暗,土院坝、土路、土墙都是灰扑扑的,只有四周的山总是新的、绿的,还让人感动。在那个生活贫穷的年代,肚子里没有多少油水的我们,从小就掌握了从大自然中觅食果腹的能力。一进山,我们的双眼和鼻子像饥饿的野兽一样灵敏,能轻松地挑选出哪些野果、野花和草根可以生吃,也能准确地辨别出哪些是无毒的蘑菇。我们曾勇敢地其实是迫于无奈地生吃过掏来的鸟蛋,也曾勇猛地用长棍捣下崖缝里的蜂巢,只为那一口甜蜜的蜂蜜。
我们那一代人的学费、家中的日常开销主要靠卖松茸得来的收入。那时候,一到雨季,村里人就起早贪黑地进山捡松茸。记得上小学时,老师带着我们上山捡蘑菇,我误打误撞地捡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朵松茸。那朵比我的小臂还粗的松茸卖了4元钱。母亲为了奖励我,用这4元钱从供销社给我买回一双绿色的凉鞋。在那个物资短缺的年代,这双漂亮的小凉鞋被同龄的孩子羡慕了好一阵子。
又一次,父母幸运地发现了一个无人光顾的菌塘,一下子就捡了半筐松茸,卖了400元钱。那个夜晚,母亲把手里的那笔“巨款”数了又数,嘴里念念有词,把自己能想到的人和物都感谢了一遍。第二天一早,父母欢天喜地地从剑川县城的骡马交易会上买回来一头小母牛。那是一头黝黑、健壮的小母牛。自从有了这头小母牛,我们家每年不仅省下了出钱请人犁地的开支,还能时不时帮助同样一贫如洗的几家亲戚。
后来的几年,靠着捡松茸、卖松茸的收入,家中又逐渐添置了简单的家具、家电,简陋的小院慢慢变得像样了。
大人早出晚归,无人管束的我们常相约去山里捡柴火、采草药、挖山基土……渴了,我们就找一处山泉伏下身子猛灌几口;饿了,我们就采一把沙棘果或马奶果嚼吃;困了,我们就找一处平坦松软的地方躺下。听着松涛、吹着山风,我们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有时一觉醒来,太阳都已西斜。
小时候,我特别喜欢听风吹松林的声音,喜欢看松林随风起伏的变化。松涛有时如海浪冲刷着沙滩一样平缓,有时又如千军万马行进一样雄浑。我时常想,为何麦浪叫“浪”,松涛却称“涛”,也许是因为这松林的波动,不似绸缎那般轻盈柔美,而更像是海浪拍打着岩石,是强劲的、有力的。
我时常躺在林间,仰头看风摇撼松树,看细密的松针相互碰撞。松针翩翩起舞,但并不是刻意跳给谁看。它们哪里知道有人在看?不过是在风的鼓舞下,不约而同地舞动,时而伴着叹息,时而伴着雀跃,仿佛在吟唱一首古老的歌曲。
有时候,我还会跟着祖父去山里寻找石头,挑选一些造型好看的带回家垒假山。那些石头山上少有树木,目光所及都是嶙峋、坚硬的岩石。那些朱褐色、青黑色的巨石安静地匍匐着,像一头头正在冬眠的怪兽。它们年复一年地仰望星空、承接雨露,身上渐渐长起青苔。我总觉得,长了青苔的岩石不能叫岩石了,因为它们似乎有了生命、呼吸。
在山中,疏离与亲密时常交织在一起。疏离的是那些沉闷的岩石,哪怕相距不过一两米,但千年万年也相对无言;亲密的是那些植物,它们的枝叶在天空中相互依偎,它们的根系在地底下缠绵交织,它们在风中不分昼夜地一直窃窃私语。
也许在某些锦衣玉食、肥马轻裘的城里人眼中,大山是沉默的、无趣的,甚至是令人恐惧的。但在我的心里,大山是沉稳的、洁净的,甚至是灵动的、鲜活的。千万年来,人们在山里获取生活所需,比如,香甜的菌菇、取暖的柴薪、肥美的野物、治病的药根、奇异的兰草……大山像一位温暖、仁厚的母亲,永远敞开它的胸怀,竭尽所能地养育着身处其中的一切生灵。
是呀,这就是大山。怎能不让我依恋和亲近。小时候进山,我总是好奇山的后面会是什么,但翻过一座山,发现前面还是山,而且,一座山和另一座山似乎也没有什么区别。
如今再进山,我已经不再去奋力攀登,也不想再去探究山的后面有什么。就停在此山、靠着此树也挺好。听着粗粝的风撼动松林,闻着熟悉的气味萦绕身边,我再一次匍匐在大山的胸膛。
我一直感谢山、怀念山。感念这些让祖祖辈辈安居乐业、挣扎谋生、生生不息的大山。我常常从山上带一把松针回来,并闻着幽幽松香默念一句:哦,原来我一直在山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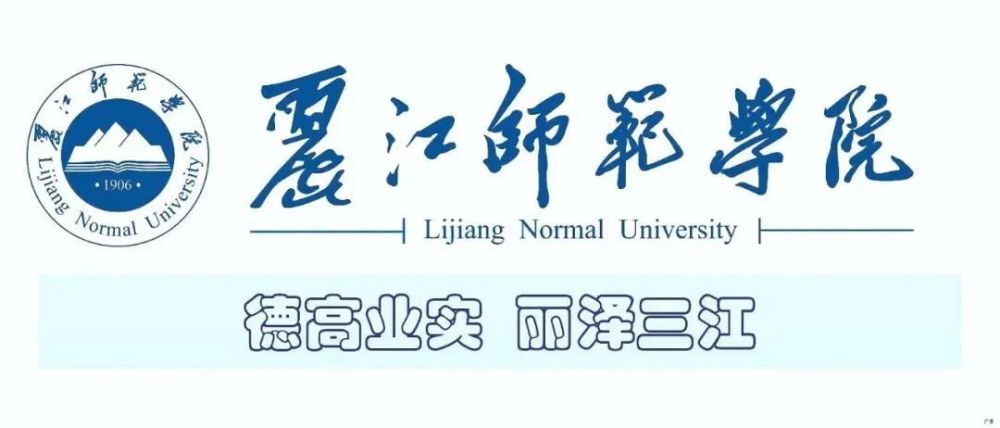

编辑:白 浩
校对:张小秋
二审:和继贤
【声明】如需转载丽江市融媒体中心名下任何平台发布的内容,请 点击这里 与我们建立有效联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