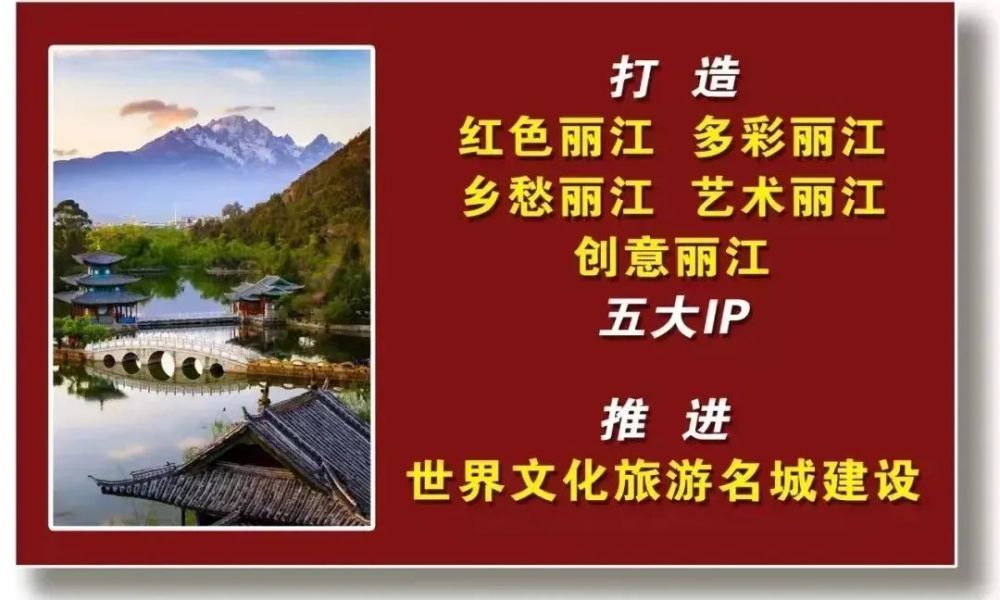
《山中逸趣序》碑考辨
杨林军(丽江师院)
碑文概述
该碑在原丽江县境内,今不得见。国家图书馆藏有拓片。碑通高45厘米、宽129厘米,刻于民国三十一年(1942年)。无题额,首题“山中逸趣序”,正文竖排30行,附文两段,宗亮东隶书作跋,和清勒石。正文后两段附文:第一段为民国三十一年万斯年所记,共9行,内容看不清楚;第二段为校长宗亮东所题,共6行,可辨。碑文内容主要记述徐霞客通过唐泰认识木增,认为木增此人非同寻常,大肆赞美木增丰功伟业。据附文说,民国时期,万斯年在丽江看到此文,遂刊刻在国立丽江师范学校内,以供全校师生学习。
碑文内容
山中逸趣序
余往交唐大来,侈谈金碧苍洱之胜。其中苞异孕灵,问出而生名世。誉满四裔,海内遥瞻,如霱云曙星,不见其人,而愿见所著述,若生白木公之《云薖集》,业行世久矣;此《山中逸趣》,又大来所手订以传者也。公世祚封侯,晋修藩伯,以雄武一军,成斩馘之功,为飞将。以金赀数万,佐军兴之急,为忠臣。以威望九鼎,落番夷之胆,为良翰。无事则诗书礼乐,有事则戎马行间,何自暇得逸于山中也?公闭意荣禄,蚤谢尘缕,学老氏之知止,同孔明之淡泊,如李西屏有子愬,吴武安有子拱,智足知兵,才堪八面,以雅镇石门铁桥,丸泥可封;使金沙之涯,俨标铜柱,无疆事之忧;故疏辞五上,天子特金币褒嘉,方许谢政。公得练巾野服,容裔于松庵雪洞中;环碧扫青,皆山也,但公世著风雅,交满天下;征文者,投诗者,购书者,以神交定盟者,嘤鸣相和;声气往来,共中原之旗鼓。银鹿青猿,走山中无虚日,公独领山中之趣于逸,有赋、有篇、有吟、有清语,拈题命韵,高矌孤闲;烟霞之色,扑人眉宇;读之,犹冷嚼梅花雪瓣也。虽然,公之逸,岂仅浪漫者;性喜博综,而樵猎于蝌漆乌铅,类陆澄刘峻。继雪山玉水之音,而接武于祖孙父子之作述,类韦弘景薛元超。精研典释,悟入宗乘,如作家禅客,类张无尽苏子瞻。是总以有余之才,与无所用之力,倍劳而得逸,因逸而成趣;讬圣世之逸民,作衣冠之巢许,非有绠瓠丝竹以娱声伎,文异锦以御鲜华;孹鳞酢龙以来奇嗜;惟椰瓢芦被,煨芋餐芝,人不知其为世臣享世禄者,洵足称山中人也。吾师乎!当读名山记,李景山有句云:“丽江雪山天下绝,积玉堆琼几千叠;足盘厚地背摩天,衡华真成两坵垤。”有山如此,公得逸于山中,非有神仙福者,岂易知山中之趣哉!是篇也,补记名山可矣。
大明崇祯霞客徐宏祖题
附文第一段不清晰。附文第二段的内容如下。
三十一年秋,国立北平图书馆万君稼轩来丽政察,将木氏珍藏徐霞客先生遗书“山中逸趣叙”勒诸贞珉,留校以垂不朽。全校师生至深欣感先生遗书如旨,光羽胄。甚珍贵,后之来者当景仰前贤而彰之。
国立丽江师范学校校长宗亮东谨识
石工和清勒石

玉龙雪山。
碑文考辨
关于这段历史的真伪,需要回溯到《徐霞客游记》中来寻找答案。据《游记》记载:徐霞客到解脱林的第三天下午,“大把事来求作所辑《云薖淡墨》序。初三日余以叙稿送进,复令大把事来谢。初四日有鸡足僧以省中录就《云薖淡墨》,缴纳木公……其所书洪武体,虽甚整而讹字极多……”就这段史料而言,前后皆为一本书,为何徐霞客写序后又说“讹字极多”呢?显然,这说的是不同的书,只是把书名弄错了。查看相关史料才发现,第一次送来的是《山中逸趣》,第二次送来的才是《云薖淡墨》。
徐霞客在《游记》中说为其作序,并流传于世。然而从徐霞客所遗留的文书来看,没有序,倒有一篇跋。关于徐霞客所写的跋,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流传有两篇。其中一篇如是说:“公世著风雅,交满天下。征文者、投诗者、购书者、以神交定盟者,嘤鸣相和,声气往来,共中原之旗鼓……生白木公示《云薖集》,业已行世久矣;此《山中逸趣》,有大来所手定以传世者……公闭意荣禄,早谢尘缨,学老氏之知止,同空明之淡泊……故,书辞五上,天子特金币褒嘉,方许谢政……银鹿青猿,走山中无虚日,公独领山中之趣于逸,有赋、有笛、有吟、有清语,拈体命韵,高旷孤闲;烟霜之色,扑入眉宇;读之,犹冷嚼梅花雨瓣也。”这很显然是一篇献给木增的颂歌,通篇充满阿谀奉承之词,被认为“可以作为木增传略看”。
从落款“宏祖”2字和内容来看,这显然不是徐霞客的文章。理由有:其一,徐霞客字弘祖,由于清乾隆皇帝名弘历,为避讳改为“宏”字。从徐霞客所作的文书时间来看,不应该改字,只可能是后人所为。其二,序与跋,都是评价该书缘起、作者特殊的经历、书的特色以及历史地位等方面的文体。序一般放在文章前面,偶有放在后面,也要取为后序,而跋都放在文章的最后。徐霞客看到此书时,已有唐泰等人作序,并已编订成册。本来像徐霞客这样的文贤,作个序不为过,但只作了个跋,便于编订,也体现了徐霞客的谦虚。其三,从文风和内容看,大有歌颂木增之丰功伟绩,这与徐霞客一贯的为人之道相悖。因此,徐霞客给《山中逸趣》写的是跋而不是序。方树梅先生由于没有看到徐霞客的真迹,便认为是徐霞客为人写的序,“海内殆无第二篇”。
其实,此跋是徐霞客在丽江为木增的诗文集《山中逸趣》撰写的一篇佳作。此文在流传过程中被一位清代贡生篡改,把章台鼎所作的序署名为徐霞客。这样的嫁接,看似可以以假乱真,想不到有多处破绽。后经数位专家多年来的不懈关注和考证,云南大学朱惠荣教授对此考究最勤,专门撰写了万余字的论文以辨明是非,扶正弯曲。当然也有人认为,此文有章台鼎借徐霞客之名来扬名之嫌,其实这样更是冤枉了章台鼎。现在,清代贡生所作的“赝品”已恢复历史的本来,实为一件令人“逸”乐之事。
《山中逸趣》是木增的一部诗赋集刊,收录有赋2篇,诗194首,是木增的得意之作。于崇祯十年(1637年)唐泰为此书作序,后来章台鼎、梁之翰、徐霞客等也分别为之作序或跋。徐霞客所作的《山中逸趣》跋,共有546字,用篆体书写,从风格和行文上与章氏截然不同。现以徐霞客所作的原文为底本,参考朱惠荣教授所著的《徐霞客与〈徐霞客游记〉》以及余嘉华教授所著的《木氏土司与丽江》相关内容,全文摘录如下。
山中逸趣跋
自两仪肇分,重者为地,重之极而山出焉。以镇定之体,奠鳌极而命方岳,但见其静秀有常而已,未有能授之逸者。熟知其体静而神自逸,其迹定而天自逸。彼夫逃形灭影,塿坯湮谷,曾是以为逸乎,穸直与山为构者也。进而求之,伊尹逸于耕,太公逸于钓,谢傅逸于奕,陶侃逸于鬲,逸不可迹求,类若此而大舜有大焉。其与木石居、鹿豕游者谁,其逸沛然决、莫能御者又谁。迹野人求之市,复迹大舜求之不得,是所谓真逸也。千古帝皇,莫不以舜为兢业,自乃鼓琴被袗,其得力于深山者固趣。但自有虞以后,山川之劳人亦久矣。神禹以之胼手胝足,秦人因之驱石范铁,焉睹所谓逸。乃丽江世公生白老先生,夙有山中逸趣者,何非天下皆劳而我独逸?天下俱悲,而我奚趣?即以天下之劳攘还之天下,而我不与之构;以我之镇定还之我,而天下阴受其庇。与山之不能相忘,我欲迹之。是山非天下之山,乃我之能镇能定之山也;多山非我一方之山,乃天下之山,而为镇能定之山也。故,文章而粗石者,逸为出岫之卷舒,云影而飞絮者,逸为天半之璚玉;泉静而滥觞者,逸为左右之逢源;丘壑而宫商之音,逸为太始赋形;而金石之宣,逸为均天。先生此集所以卷纶藏密者,与莘渭各异而镇意念之心,故悠然迹外,即纳之大麓,又何与于舜庭之扬歌。垂承则能赍天下于春台者此趣,能翔太和于寰宇者此趣,而山中云乎哉?然必系之山中者,所以奠鳌极而?方岳也。弘祖遍觅山于天下,而亦乃得逸于山中,故喜极而为之序。
崇祯己卯仲春朔旦
江左教下后学徐弘祖霞逸父顿首拜书于解脱檀林

群山。
徐霞客所作的《山中逸趣》跋,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跋,而是一篇借题阐述天地变迁、人情世故的精华篇章。徐霞客不愧为地理学家,用地学眼光和思想观察山川变迁,承认地壳运动是地表凸凹不平的原因。“重者为地,重之极而山出焉。以镇定之体,奠鳌极而命方岳”,“彼夫逃形灭影,塿坯湮谷,曾是以为逸乎,穸(是)直与山为构也。”随着人类不断参与地表形状改变,因而就有了“自有虞以后,山川之劳人亦久矣。”
接着,他抒发了自己游历山川30年来所积累起来的深邃的哲理。运用运动与静止的观点,“见其静秀有常而已,未有能授之逸者”“孰知其体静而神自逸,其迹定而天自逸”,这就是说,“体”“迹”决定“神”“天”,讲到人世间的和谐问题。“以奠鳌极而命方岳也”,从表述自然变化规律转入人世间,“进而求之,伊尹逸于耕,太公逸于钓,谢傅逸于奕,陶侃逸于鬲”。至此,他道出了自然界与人类一样也需要保持和谐,方能找到“逸”即平衡,一旦失去平衡,人类只好改造和防御一些自然变化,“神禹以之胼手胝足,秦人因之驱石范铁,焉睹所谓逸。”大禹治水,三过家门而不入,因为常年接触水,手脚掌都长出一层厚厚的老茧;秦国人垒起石头,再铸上铁水以防水患。这些怎么能说是“逸”呢?
笔锋一转,他谈起木增的生活情趣。“夙有山中逸趣者何?”徐霞客结合木增戎马半生的经历,说明木增并非逃离人间世事而避居山林,“非天下皆劳,而我独逸,天下俱悲,而我欲趣。即以天下之劳攘还天下,而我不与之构;以我之镇定还之我,而天下阴受其庇”。袁宏道在《叙陈正甫会心集》中言:“人所难得者唯趣。趣如山上之色,水中之味,花中之光,女中之态,虽善说者不能一语,唯会心者知之。”木增也好,徐霞客本人也好,祖国大好河山并非为某人所独占,而是“是山非天下之山,乃我之能镇能定之山也;多山非我一方之山,乃天下之山,而为镇、为定之山也”。道出了徐霞客同木增共同情趣和爱好,知己难求!木增也曾作诗曰:“我爱芝山景最佳,屡经甲子不思家。此中饮食殊人世,辟谷常吞日月华。”
自然界和人世间有众多和谐的景象。“文章而觕石者,逸为出岫之卷舒,雪影而飞絮者,逸为天半之璚玉;泉静而滥觞者,逸为左右之逢源;志情而宫商之音,逸为太始赋形;而金石之宣,逸为均天。”也就是说,“各美其美”方能找到事物存在的合理之处。木增的大作《山中逸趣》表现出了“卷纶藏密者,与莘渭各异而镇意念之心,故悠然迹外”。这么好的文章可与天高地渊作比较,它本身就具备了这样的内容和精神。“然必系之山中者,所以奠鳌极而命方岳也。”道出了只有有心人才能知道这些自然变化。最后,徐霞客很委婉地道出了一生的行世准则和心灵深处的向往,“弘祖遍觅山于天下,而亦乃得逸于山中,故,喜极而为之序。”
此跋道出了徐霞客在半生游历中的深刻感悟。因此,此文不如说是徐霞客对自然、人类活动规律作一次“表白”。对明末社会动荡不安、民不聊生作了暗示,并指出了处理办法:“千古帝皇,莫不以舜为兢业,自乃鼓琴被袗,其得力于深山者固趣。”体现了一位看似不闻政事的游客,实则是关心民事、呼吁社会和谐的社会活动家。
此文能有如此深刻、富有深邃哲理的跋,确实体现了徐霞客与木增都是好山水逸趣之人,有着共同的情趣。因而,从一个侧面道出了徐霞客不虚此行的感慨溢于言表。纳西族土司木增在边远之地能有如此的感悟,徐霞客深为其动容,故而作此文以示后人。
说句题外话。当年万斯年以为这是徐霞客的真迹,推荐给时任国立丽江师范学校校长宗亮东,后者用巨石刊刻后立于校园供全校师生学习。做这件事的出发点是好的,结果却造成错讹。
图片由周侃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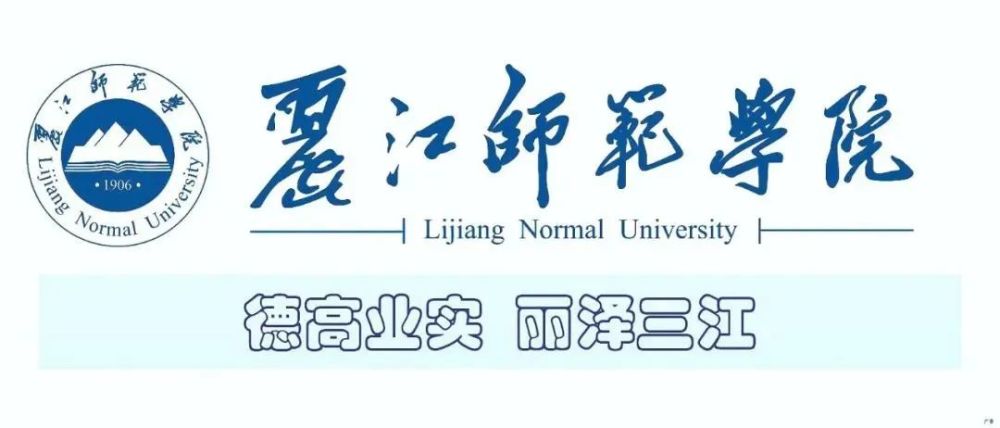

编辑:白 浩
校对:张小秋
二审:和继贤
【声明】如需转载丽江市融媒体中心名下任何平台发布的内容,请 点击这里 与我们建立有效联系。